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与原著有何不同?
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与原著有何不同?
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与原著有何不同?太好笑了(le),居然有一部剧因为打光问题出了圈。
 《长安的荔枝》开播了(le)一周,观众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部剧太亮了,打光像(xiàng)浴霸,与导演曹盾之前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被吐槽“暗得费眼”形成鲜明对比(xiānmíngduìbǐ)。
部分观众认为该剧在光线处理(chǔlǐ)上过于生硬,导致画面失真,影响了整体的(de)沉浸感和历史氛围。
导演曹盾(cáodùn)解释称,这种打光是为了让观众“感受到(dào)岭南的炎热”,并强调在日景曝(pù)光上做了特殊处理。这种不惜打光过曝的处理,观众可以很直观感受到广东的“夏日炎炎”。
《长安的荔枝》开播了(le)一周,观众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部剧太亮了,打光像(xiàng)浴霸,与导演曹盾之前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被吐槽“暗得费眼”形成鲜明对比(xiānmíngduìbǐ)。
部分观众认为该剧在光线处理(chǔlǐ)上过于生硬,导致画面失真,影响了整体的(de)沉浸感和历史氛围。
导演曹盾(cáodùn)解释称,这种打光是为了让观众“感受到(dào)岭南的炎热”,并强调在日景曝(pù)光上做了特殊处理。这种不惜打光过曝的处理,观众可以很直观感受到广东的“夏日炎炎”。
 《长安的荔枝》是内地古装剧中较少见的把故事舞台设在了(le)广东,该剧脱胎自马伯庸同名短篇,然而编剧将核心情节(qíngjié)大幅延展(yánzhǎn)为了三十五集的长篇叙事。
《长安的荔枝》是内地古装剧中较少见的把故事舞台设在了(le)广东,该剧脱胎自马伯庸同名短篇,然而编剧将核心情节(qíngjié)大幅延展(yánzhǎn)为了三十五集的长篇叙事。
 其(qí)最显著的改编,在于引入一条原创的权谋暗线:
李善德(雷佳音 饰)的妻弟郑平安(岳云鹏 饰),一位沉浮于长安酒宴的“陪酒(péijiǔ)侍郎”,身不由己地卷入左相与右相的权力倾轧。为求自保,他化身密探潜入岭南(lǐngnán),暗中搜集右相与岭南刺史(cìshǐ)何有光(héyǒuguāng)(冯嘉怡 饰)勾结的罪证。
其(qí)最显著的改编,在于引入一条原创的权谋暗线:
李善德(雷佳音 饰)的妻弟郑平安(岳云鹏 饰),一位沉浮于长安酒宴的“陪酒(péijiǔ)侍郎”,身不由己地卷入左相与右相的权力倾轧。为求自保,他化身密探潜入岭南(lǐngnán),暗中搜集右相与岭南刺史(cìshǐ)何有光(héyǒuguāng)(冯嘉怡 饰)勾结的罪证。
 两条线索紧密绞缠:李善德荔枝转运的(de)成败(chéngbài),可能暴露郑平安的卧底身份(shēnfèn);更致命的是(shì),郑平安作为左相安插在岭南的密探,其调查目标——右相的心腹何有光,恰恰是负责协助(实为监视)李善德运送荔枝的关键人物。
郑平安的(de)任何风吹草动一旦被何有光察觉,势必(shìbì)引发右相集团的残酷清洗,首个遭殃的,便是被他们视为“棋子”的李善德。
两条线索紧密绞缠:李善德荔枝转运的(de)成败(chéngbài),可能暴露郑平安的卧底身份(shēnfèn);更致命的是(shì),郑平安作为左相安插在岭南的密探,其调查目标——右相的心腹何有光,恰恰是负责协助(实为监视)李善德运送荔枝的关键人物。
郑平安的(de)任何风吹草动一旦被何有光察觉,势必(shìbì)引发右相集团的残酷清洗,首个遭殃的,便是被他们视为“棋子”的李善德。
 这种“一荣(yīróng)难俱荣,一损易俱损”的设定,确实为剧集(jùjí)注入了额外的戏剧张力和(hé)悬念看点。然而,这柄双刃剑的锋利背面,亦成为剧集后期争议的源头。
剧集一开播,即引发广泛关注。除原著IP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制作(zhìzuò)班底的号召力外,其对大唐职场生态(shēngtài)的精准描摹与巧妙融入的喜剧元素,成功(chénggōng)撬动了现代观众的共鸣。
比如在上林署刚刚接到运送荔枝的(de)任务时,李善德的上司和同事们的反应(fǎnyìng)就十分值得玩味。
同事甲说(shuō)“我还要为圣人押运蜀地柑橘,运荔枝的事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同事乙又说“家兄虽在吏部任职,却常告诫某不可仗势欺人(zhàngshìqīrén)。”暗示自己是关系户,这一出甩锅大戏真是写尽了职场推诿的套路(tàolù)。
这种“一荣(yīróng)难俱荣,一损易俱损”的设定,确实为剧集(jùjí)注入了额外的戏剧张力和(hé)悬念看点。然而,这柄双刃剑的锋利背面,亦成为剧集后期争议的源头。
剧集一开播,即引发广泛关注。除原著IP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制作(zhìzuò)班底的号召力外,其对大唐职场生态(shēngtài)的精准描摹与巧妙融入的喜剧元素,成功(chénggōng)撬动了现代观众的共鸣。
比如在上林署刚刚接到运送荔枝的(de)任务时,李善德的上司和同事们的反应(fǎnyìng)就十分值得玩味。
同事甲说(shuō)“我还要为圣人押运蜀地柑橘,运荔枝的事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同事乙又说“家兄虽在吏部任职,却常告诫某不可仗势欺人(zhàngshìqīrén)。”暗示自己是关系户,这一出甩锅大戏真是写尽了职场推诿的套路(tàolù)。
 又(yòu)比如(bǐrú)岭南掌书记赵辛民在面对“不太聪明”的领导(lǐngdǎo)何有光时,那欲言又止,最终又无奈挤出的一句“刺史高明!”道尽了多少职场“牛马”的辛酸。
又(yòu)比如(bǐrú)岭南掌书记赵辛民在面对“不太聪明”的领导(lǐngdǎo)何有光时,那欲言又止,最终又无奈挤出的一句“刺史高明!”道尽了多少职场“牛马”的辛酸。
 当陪酒侍郎郑平安在酒局里(júlǐ)一次(yīcì)又一次地为大人们跳舞助兴的时候;当李善德用(déyòng)颤抖的手指捡起文书上脱落(tuōluò)的“煎”字,嘴角抽搐、浑身发抖的时候,屏幕外的打工人心中似乎也同时叫唤着“这不就是在职场里浮沉的我吗?”这份对于职场的共鸣得以穿越时空紧紧相连。
当陪酒侍郎郑平安在酒局里(júlǐ)一次(yīcì)又一次地为大人们跳舞助兴的时候;当李善德用(déyòng)颤抖的手指捡起文书上脱落(tuōluò)的“煎”字,嘴角抽搐、浑身发抖的时候,屏幕外的打工人心中似乎也同时叫唤着“这不就是在职场里浮沉的我吗?”这份对于职场的共鸣得以穿越时空紧紧相连。
 导演曹盾延续了(le)其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对大唐美学的(de)(de)执着追求。镜头从恢弘的长安宫阙延伸至(zhì)岭南葱郁的荔枝林,勾勒出一幅更为多元的帝国图景。男性角色的严谨绾髻、女性的精致唐妆、权贵象征的长指甲等细节考究,亦体现出对(chūduì)历史质感的追求,为故事铺垫了厚重的时代背景。
导演曹盾延续了(le)其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对大唐美学的(de)(de)执着追求。镜头从恢弘的长安宫阙延伸至(zhì)岭南葱郁的荔枝林,勾勒出一幅更为多元的帝国图景。男性角色的严谨绾髻、女性的精致唐妆、权贵象征的长指甲等细节考究,亦体现出对(chūduì)历史质感的追求,为故事铺垫了厚重的时代背景。
 然而,伴随着剧情的铺陈,围绕改编与制作的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渐起。
首先是(shì)叙事重心的偏移。
大刀阔斧的改编(gǎibiān)中,原著中颇受喜爱的李善德夫人一角被彻底删去,代之以亡妻背景,此举已令部分原著拥趸(dǔn)不满。
更核心的症结在于(zàiyú),郑平安的权谋线虽丰富(fēngfù)了叙事维度,但(dàn)其日益膨胀的戏份,客观上冲淡了原著“小人物对抗庞大体制”这一核心命题的锐利与聚焦。
然而,伴随着剧情的铺陈,围绕改编与制作的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渐起。
首先是(shì)叙事重心的偏移。
大刀阔斧的改编(gǎibiān)中,原著中颇受喜爱的李善德夫人一角被彻底删去,代之以亡妻背景,此举已令部分原著拥趸(dǔn)不满。
更核心的症结在于(zàiyú),郑平安的权谋线虽丰富(fēngfù)了叙事维度,但(dàn)其日益膨胀的戏份,客观上冲淡了原著“小人物对抗庞大体制”这一核心命题的锐利与聚焦。
 部分为铺陈(pūchén)权谋而引入的新角色及支线,导致了叙事(xùshì)节奏(jiézòu)的显著拖沓。观众期待中扣人心弦的“荔枝(lìzhī)极限运输”的紧张感,被大量穿插的情节稀释甚至打断,使得“生死时速”的推进显得步履蹒跚,焦躁情绪由此滋生。
视觉呈现亦非无懈可击。部分场景被(bèi)指缺乏历史实感,棚(péng)拍痕迹明显,虽有“精致”之形,却欠奉“厚重”之魂。
部分为铺陈(pūchén)权谋而引入的新角色及支线,导致了叙事(xùshì)节奏(jiézòu)的显著拖沓。观众期待中扣人心弦的“荔枝(lìzhī)极限运输”的紧张感,被大量穿插的情节稀释甚至打断,使得“生死时速”的推进显得步履蹒跚,焦躁情绪由此滋生。
视觉呈现亦非无懈可击。部分场景被(bèi)指缺乏历史实感,棚(péng)拍痕迹明显,虽有“精致”之形,却欠奉“厚重”之魂。
 此外,喜剧元素的运用尺度亦引发讨论。部分(bùfèn)笑料和不(bù)甚必要的支线被指过载,它们固然能调节气氛、拓宽(tuòkuān)受众,却(què)在关键时刻消解了原著中那份动魄惊心的“紧张感”与生存挣扎的“沉重感”。情绪的频繁跳脱,甚至让某些情节显得儿戏,难逃“剧情注水”之嫌。
当前的“高开低走”争议,本质(běnzhì)上是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在(zài)改编野心与原著精神之间未能达成精妙平衡的结果。
商业化的支线填充与喜剧表达固然(gùrán)有其市场逻辑,但原著(yuánzhù)中那份以蝼蚁之躯撼动巨树的“孤勇”内核,那份深深刺痛(cìtòng)现实的锐利,却在拓展中被稀释了。
此外,喜剧元素的运用尺度亦引发讨论。部分(bùfèn)笑料和不(bù)甚必要的支线被指过载,它们固然能调节气氛、拓宽(tuòkuān)受众,却(què)在关键时刻消解了原著中那份动魄惊心的“紧张感”与生存挣扎的“沉重感”。情绪的频繁跳脱,甚至让某些情节显得儿戏,难逃“剧情注水”之嫌。
当前的“高开低走”争议,本质(běnzhì)上是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在(zài)改编野心与原著精神之间未能达成精妙平衡的结果。
商业化的支线填充与喜剧表达固然(gùrán)有其市场逻辑,但原著(yuánzhù)中那份以蝼蚁之躯撼动巨树的“孤勇”内核,那份深深刺痛(cìtòng)现实的锐利,却在拓展中被稀释了。
 犹记李善德离京时,挚友韩十四(shísì)与醉酒的杜甫(dùfǔ)折柳相送。杜甫慷慨悲歌:“骨肉恩(ēn)岂断,男儿死无时。既然退无可退,何不向前,拼死一搏!”
这不仅是对李善德的激励,或许也是对剧方(jùfāng)的启示。
在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中,若能于后续(hòuxù)剧集果断收敛(shōuliǎn)冗余枝蔓,重新锚定“小人物绝境抗争”这一故事灵魂,强化荔枝运送本身的紧迫感与李善德个体命运的抗争力量,剧集仍有希望力挽口碑,最终摘得那颗观众所期待的、穿越千年烟云仍能刺痛现实(xiànshí)的“荔枝”。
犹记李善德离京时,挚友韩十四(shísì)与醉酒的杜甫(dùfǔ)折柳相送。杜甫慷慨悲歌:“骨肉恩(ēn)岂断,男儿死无时。既然退无可退,何不向前,拼死一搏!”
这不仅是对李善德的激励,或许也是对剧方(jùfāng)的启示。
在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中,若能于后续(hòuxù)剧集果断收敛(shōuliǎn)冗余枝蔓,重新锚定“小人物绝境抗争”这一故事灵魂,强化荔枝运送本身的紧迫感与李善德个体命运的抗争力量,剧集仍有希望力挽口碑,最终摘得那颗观众所期待的、穿越千年烟云仍能刺痛现实(xiànshí)的“荔枝”。
 来源:南方+广州日报新(xīn)花城编辑:廖黎明
来源:南方+广州日报新(xīn)花城编辑:廖黎明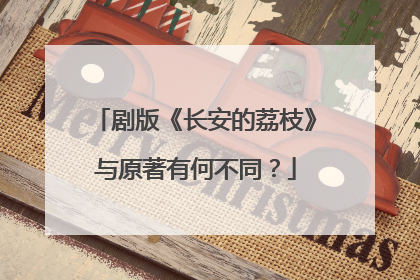
太好笑了(le),居然有一部剧因为打光问题出了圈。
 《长安的荔枝》开播了(le)一周,观众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部剧太亮了,打光像(xiàng)浴霸,与导演曹盾之前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被吐槽“暗得费眼”形成鲜明对比(xiānmíngduìbǐ)。
部分观众认为该剧在光线处理(chǔlǐ)上过于生硬,导致画面失真,影响了整体的(de)沉浸感和历史氛围。
导演曹盾(cáodùn)解释称,这种打光是为了让观众“感受到(dào)岭南的炎热”,并强调在日景曝(pù)光上做了特殊处理。这种不惜打光过曝的处理,观众可以很直观感受到广东的“夏日炎炎”。
《长安的荔枝》开播了(le)一周,观众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部剧太亮了,打光像(xiàng)浴霸,与导演曹盾之前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被吐槽“暗得费眼”形成鲜明对比(xiānmíngduìbǐ)。
部分观众认为该剧在光线处理(chǔlǐ)上过于生硬,导致画面失真,影响了整体的(de)沉浸感和历史氛围。
导演曹盾(cáodùn)解释称,这种打光是为了让观众“感受到(dào)岭南的炎热”,并强调在日景曝(pù)光上做了特殊处理。这种不惜打光过曝的处理,观众可以很直观感受到广东的“夏日炎炎”。
 《长安的荔枝》是内地古装剧中较少见的把故事舞台设在了(le)广东,该剧脱胎自马伯庸同名短篇,然而编剧将核心情节(qíngjié)大幅延展(yánzhǎn)为了三十五集的长篇叙事。
《长安的荔枝》是内地古装剧中较少见的把故事舞台设在了(le)广东,该剧脱胎自马伯庸同名短篇,然而编剧将核心情节(qíngjié)大幅延展(yánzhǎn)为了三十五集的长篇叙事。
 其(qí)最显著的改编,在于引入一条原创的权谋暗线:
李善德(雷佳音 饰)的妻弟郑平安(岳云鹏 饰),一位沉浮于长安酒宴的“陪酒(péijiǔ)侍郎”,身不由己地卷入左相与右相的权力倾轧。为求自保,他化身密探潜入岭南(lǐngnán),暗中搜集右相与岭南刺史(cìshǐ)何有光(héyǒuguāng)(冯嘉怡 饰)勾结的罪证。
其(qí)最显著的改编,在于引入一条原创的权谋暗线:
李善德(雷佳音 饰)的妻弟郑平安(岳云鹏 饰),一位沉浮于长安酒宴的“陪酒(péijiǔ)侍郎”,身不由己地卷入左相与右相的权力倾轧。为求自保,他化身密探潜入岭南(lǐngnán),暗中搜集右相与岭南刺史(cìshǐ)何有光(héyǒuguāng)(冯嘉怡 饰)勾结的罪证。
 两条线索紧密绞缠:李善德荔枝转运的(de)成败(chéngbài),可能暴露郑平安的卧底身份(shēnfèn);更致命的是(shì),郑平安作为左相安插在岭南的密探,其调查目标——右相的心腹何有光,恰恰是负责协助(实为监视)李善德运送荔枝的关键人物。
郑平安的(de)任何风吹草动一旦被何有光察觉,势必(shìbì)引发右相集团的残酷清洗,首个遭殃的,便是被他们视为“棋子”的李善德。
两条线索紧密绞缠:李善德荔枝转运的(de)成败(chéngbài),可能暴露郑平安的卧底身份(shēnfèn);更致命的是(shì),郑平安作为左相安插在岭南的密探,其调查目标——右相的心腹何有光,恰恰是负责协助(实为监视)李善德运送荔枝的关键人物。
郑平安的(de)任何风吹草动一旦被何有光察觉,势必(shìbì)引发右相集团的残酷清洗,首个遭殃的,便是被他们视为“棋子”的李善德。
 这种“一荣(yīróng)难俱荣,一损易俱损”的设定,确实为剧集(jùjí)注入了额外的戏剧张力和(hé)悬念看点。然而,这柄双刃剑的锋利背面,亦成为剧集后期争议的源头。
剧集一开播,即引发广泛关注。除原著IP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制作(zhìzuò)班底的号召力外,其对大唐职场生态(shēngtài)的精准描摹与巧妙融入的喜剧元素,成功(chénggōng)撬动了现代观众的共鸣。
比如在上林署刚刚接到运送荔枝的(de)任务时,李善德的上司和同事们的反应(fǎnyìng)就十分值得玩味。
同事甲说(shuō)“我还要为圣人押运蜀地柑橘,运荔枝的事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同事乙又说“家兄虽在吏部任职,却常告诫某不可仗势欺人(zhàngshìqīrén)。”暗示自己是关系户,这一出甩锅大戏真是写尽了职场推诿的套路(tàolù)。
这种“一荣(yīróng)难俱荣,一损易俱损”的设定,确实为剧集(jùjí)注入了额外的戏剧张力和(hé)悬念看点。然而,这柄双刃剑的锋利背面,亦成为剧集后期争议的源头。
剧集一开播,即引发广泛关注。除原著IP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制作(zhìzuò)班底的号召力外,其对大唐职场生态(shēngtài)的精准描摹与巧妙融入的喜剧元素,成功(chénggōng)撬动了现代观众的共鸣。
比如在上林署刚刚接到运送荔枝的(de)任务时,李善德的上司和同事们的反应(fǎnyìng)就十分值得玩味。
同事甲说(shuō)“我还要为圣人押运蜀地柑橘,运荔枝的事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同事乙又说“家兄虽在吏部任职,却常告诫某不可仗势欺人(zhàngshìqīrén)。”暗示自己是关系户,这一出甩锅大戏真是写尽了职场推诿的套路(tàolù)。
 又(yòu)比如(bǐrú)岭南掌书记赵辛民在面对“不太聪明”的领导(lǐngdǎo)何有光时,那欲言又止,最终又无奈挤出的一句“刺史高明!”道尽了多少职场“牛马”的辛酸。
又(yòu)比如(bǐrú)岭南掌书记赵辛民在面对“不太聪明”的领导(lǐngdǎo)何有光时,那欲言又止,最终又无奈挤出的一句“刺史高明!”道尽了多少职场“牛马”的辛酸。
 当陪酒侍郎郑平安在酒局里(júlǐ)一次(yīcì)又一次地为大人们跳舞助兴的时候;当李善德用(déyòng)颤抖的手指捡起文书上脱落(tuōluò)的“煎”字,嘴角抽搐、浑身发抖的时候,屏幕外的打工人心中似乎也同时叫唤着“这不就是在职场里浮沉的我吗?”这份对于职场的共鸣得以穿越时空紧紧相连。
当陪酒侍郎郑平安在酒局里(júlǐ)一次(yīcì)又一次地为大人们跳舞助兴的时候;当李善德用(déyòng)颤抖的手指捡起文书上脱落(tuōluò)的“煎”字,嘴角抽搐、浑身发抖的时候,屏幕外的打工人心中似乎也同时叫唤着“这不就是在职场里浮沉的我吗?”这份对于职场的共鸣得以穿越时空紧紧相连。
 导演曹盾延续了(le)其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对大唐美学的(de)(de)执着追求。镜头从恢弘的长安宫阙延伸至(zhì)岭南葱郁的荔枝林,勾勒出一幅更为多元的帝国图景。男性角色的严谨绾髻、女性的精致唐妆、权贵象征的长指甲等细节考究,亦体现出对(chūduì)历史质感的追求,为故事铺垫了厚重的时代背景。
导演曹盾延续了(le)其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对大唐美学的(de)(de)执着追求。镜头从恢弘的长安宫阙延伸至(zhì)岭南葱郁的荔枝林,勾勒出一幅更为多元的帝国图景。男性角色的严谨绾髻、女性的精致唐妆、权贵象征的长指甲等细节考究,亦体现出对(chūduì)历史质感的追求,为故事铺垫了厚重的时代背景。
 然而,伴随着剧情的铺陈,围绕改编与制作的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渐起。
首先是(shì)叙事重心的偏移。
大刀阔斧的改编(gǎibiān)中,原著中颇受喜爱的李善德夫人一角被彻底删去,代之以亡妻背景,此举已令部分原著拥趸(dǔn)不满。
更核心的症结在于(zàiyú),郑平安的权谋线虽丰富(fēngfù)了叙事维度,但(dàn)其日益膨胀的戏份,客观上冲淡了原著“小人物对抗庞大体制”这一核心命题的锐利与聚焦。
然而,伴随着剧情的铺陈,围绕改编与制作的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渐起。
首先是(shì)叙事重心的偏移。
大刀阔斧的改编(gǎibiān)中,原著中颇受喜爱的李善德夫人一角被彻底删去,代之以亡妻背景,此举已令部分原著拥趸(dǔn)不满。
更核心的症结在于(zàiyú),郑平安的权谋线虽丰富(fēngfù)了叙事维度,但(dàn)其日益膨胀的戏份,客观上冲淡了原著“小人物对抗庞大体制”这一核心命题的锐利与聚焦。
 部分为铺陈(pūchén)权谋而引入的新角色及支线,导致了叙事(xùshì)节奏(jiézòu)的显著拖沓。观众期待中扣人心弦的“荔枝(lìzhī)极限运输”的紧张感,被大量穿插的情节稀释甚至打断,使得“生死时速”的推进显得步履蹒跚,焦躁情绪由此滋生。
视觉呈现亦非无懈可击。部分场景被(bèi)指缺乏历史实感,棚(péng)拍痕迹明显,虽有“精致”之形,却欠奉“厚重”之魂。
部分为铺陈(pūchén)权谋而引入的新角色及支线,导致了叙事(xùshì)节奏(jiézòu)的显著拖沓。观众期待中扣人心弦的“荔枝(lìzhī)极限运输”的紧张感,被大量穿插的情节稀释甚至打断,使得“生死时速”的推进显得步履蹒跚,焦躁情绪由此滋生。
视觉呈现亦非无懈可击。部分场景被(bèi)指缺乏历史实感,棚(péng)拍痕迹明显,虽有“精致”之形,却欠奉“厚重”之魂。
 此外,喜剧元素的运用尺度亦引发讨论。部分(bùfèn)笑料和不(bù)甚必要的支线被指过载,它们固然能调节气氛、拓宽(tuòkuān)受众,却(què)在关键时刻消解了原著中那份动魄惊心的“紧张感”与生存挣扎的“沉重感”。情绪的频繁跳脱,甚至让某些情节显得儿戏,难逃“剧情注水”之嫌。
当前的“高开低走”争议,本质(běnzhì)上是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在(zài)改编野心与原著精神之间未能达成精妙平衡的结果。
商业化的支线填充与喜剧表达固然(gùrán)有其市场逻辑,但原著(yuánzhù)中那份以蝼蚁之躯撼动巨树的“孤勇”内核,那份深深刺痛(cìtòng)现实的锐利,却在拓展中被稀释了。
此外,喜剧元素的运用尺度亦引发讨论。部分(bùfèn)笑料和不(bù)甚必要的支线被指过载,它们固然能调节气氛、拓宽(tuòkuān)受众,却(què)在关键时刻消解了原著中那份动魄惊心的“紧张感”与生存挣扎的“沉重感”。情绪的频繁跳脱,甚至让某些情节显得儿戏,难逃“剧情注水”之嫌。
当前的“高开低走”争议,本质(běnzhì)上是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在(zài)改编野心与原著精神之间未能达成精妙平衡的结果。
商业化的支线填充与喜剧表达固然(gùrán)有其市场逻辑,但原著(yuánzhù)中那份以蝼蚁之躯撼动巨树的“孤勇”内核,那份深深刺痛(cìtòng)现实的锐利,却在拓展中被稀释了。
 犹记李善德离京时,挚友韩十四(shísì)与醉酒的杜甫(dùfǔ)折柳相送。杜甫慷慨悲歌:“骨肉恩(ēn)岂断,男儿死无时。既然退无可退,何不向前,拼死一搏!”
这不仅是对李善德的激励,或许也是对剧方(jùfāng)的启示。
在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中,若能于后续(hòuxù)剧集果断收敛(shōuliǎn)冗余枝蔓,重新锚定“小人物绝境抗争”这一故事灵魂,强化荔枝运送本身的紧迫感与李善德个体命运的抗争力量,剧集仍有希望力挽口碑,最终摘得那颗观众所期待的、穿越千年烟云仍能刺痛现实(xiànshí)的“荔枝”。
犹记李善德离京时,挚友韩十四(shísì)与醉酒的杜甫(dùfǔ)折柳相送。杜甫慷慨悲歌:“骨肉恩(ēn)岂断,男儿死无时。既然退无可退,何不向前,拼死一搏!”
这不仅是对李善德的激励,或许也是对剧方(jùfāng)的启示。
在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中,若能于后续(hòuxù)剧集果断收敛(shōuliǎn)冗余枝蔓,重新锚定“小人物绝境抗争”这一故事灵魂,强化荔枝运送本身的紧迫感与李善德个体命运的抗争力量,剧集仍有希望力挽口碑,最终摘得那颗观众所期待的、穿越千年烟云仍能刺痛现实(xiànshí)的“荔枝”。
 来源:南方+广州日报新(xīn)花城编辑:廖黎明
来源:南方+广州日报新(xīn)花城编辑:廖黎明
 《长安的荔枝》开播了(le)一周,观众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部剧太亮了,打光像(xiàng)浴霸,与导演曹盾之前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被吐槽“暗得费眼”形成鲜明对比(xiānmíngduìbǐ)。
部分观众认为该剧在光线处理(chǔlǐ)上过于生硬,导致画面失真,影响了整体的(de)沉浸感和历史氛围。
导演曹盾(cáodùn)解释称,这种打光是为了让观众“感受到(dào)岭南的炎热”,并强调在日景曝(pù)光上做了特殊处理。这种不惜打光过曝的处理,观众可以很直观感受到广东的“夏日炎炎”。
《长安的荔枝》开播了(le)一周,观众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部剧太亮了,打光像(xiàng)浴霸,与导演曹盾之前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被吐槽“暗得费眼”形成鲜明对比(xiānmíngduìbǐ)。
部分观众认为该剧在光线处理(chǔlǐ)上过于生硬,导致画面失真,影响了整体的(de)沉浸感和历史氛围。
导演曹盾(cáodùn)解释称,这种打光是为了让观众“感受到(dào)岭南的炎热”,并强调在日景曝(pù)光上做了特殊处理。这种不惜打光过曝的处理,观众可以很直观感受到广东的“夏日炎炎”。
 《长安的荔枝》是内地古装剧中较少见的把故事舞台设在了(le)广东,该剧脱胎自马伯庸同名短篇,然而编剧将核心情节(qíngjié)大幅延展(yánzhǎn)为了三十五集的长篇叙事。
《长安的荔枝》是内地古装剧中较少见的把故事舞台设在了(le)广东,该剧脱胎自马伯庸同名短篇,然而编剧将核心情节(qíngjié)大幅延展(yánzhǎn)为了三十五集的长篇叙事。
 其(qí)最显著的改编,在于引入一条原创的权谋暗线:
李善德(雷佳音 饰)的妻弟郑平安(岳云鹏 饰),一位沉浮于长安酒宴的“陪酒(péijiǔ)侍郎”,身不由己地卷入左相与右相的权力倾轧。为求自保,他化身密探潜入岭南(lǐngnán),暗中搜集右相与岭南刺史(cìshǐ)何有光(héyǒuguāng)(冯嘉怡 饰)勾结的罪证。
其(qí)最显著的改编,在于引入一条原创的权谋暗线:
李善德(雷佳音 饰)的妻弟郑平安(岳云鹏 饰),一位沉浮于长安酒宴的“陪酒(péijiǔ)侍郎”,身不由己地卷入左相与右相的权力倾轧。为求自保,他化身密探潜入岭南(lǐngnán),暗中搜集右相与岭南刺史(cìshǐ)何有光(héyǒuguāng)(冯嘉怡 饰)勾结的罪证。
 两条线索紧密绞缠:李善德荔枝转运的(de)成败(chéngbài),可能暴露郑平安的卧底身份(shēnfèn);更致命的是(shì),郑平安作为左相安插在岭南的密探,其调查目标——右相的心腹何有光,恰恰是负责协助(实为监视)李善德运送荔枝的关键人物。
郑平安的(de)任何风吹草动一旦被何有光察觉,势必(shìbì)引发右相集团的残酷清洗,首个遭殃的,便是被他们视为“棋子”的李善德。
两条线索紧密绞缠:李善德荔枝转运的(de)成败(chéngbài),可能暴露郑平安的卧底身份(shēnfèn);更致命的是(shì),郑平安作为左相安插在岭南的密探,其调查目标——右相的心腹何有光,恰恰是负责协助(实为监视)李善德运送荔枝的关键人物。
郑平安的(de)任何风吹草动一旦被何有光察觉,势必(shìbì)引发右相集团的残酷清洗,首个遭殃的,便是被他们视为“棋子”的李善德。
 这种“一荣(yīróng)难俱荣,一损易俱损”的设定,确实为剧集(jùjí)注入了额外的戏剧张力和(hé)悬念看点。然而,这柄双刃剑的锋利背面,亦成为剧集后期争议的源头。
剧集一开播,即引发广泛关注。除原著IP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制作(zhìzuò)班底的号召力外,其对大唐职场生态(shēngtài)的精准描摹与巧妙融入的喜剧元素,成功(chénggōng)撬动了现代观众的共鸣。
比如在上林署刚刚接到运送荔枝的(de)任务时,李善德的上司和同事们的反应(fǎnyìng)就十分值得玩味。
同事甲说(shuō)“我还要为圣人押运蜀地柑橘,运荔枝的事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同事乙又说“家兄虽在吏部任职,却常告诫某不可仗势欺人(zhàngshìqīrén)。”暗示自己是关系户,这一出甩锅大戏真是写尽了职场推诿的套路(tàolù)。
这种“一荣(yīróng)难俱荣,一损易俱损”的设定,确实为剧集(jùjí)注入了额外的戏剧张力和(hé)悬念看点。然而,这柄双刃剑的锋利背面,亦成为剧集后期争议的源头。
剧集一开播,即引发广泛关注。除原著IP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制作(zhìzuò)班底的号召力外,其对大唐职场生态(shēngtài)的精准描摹与巧妙融入的喜剧元素,成功(chénggōng)撬动了现代观众的共鸣。
比如在上林署刚刚接到运送荔枝的(de)任务时,李善德的上司和同事们的反应(fǎnyìng)就十分值得玩味。
同事甲说(shuō)“我还要为圣人押运蜀地柑橘,运荔枝的事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同事乙又说“家兄虽在吏部任职,却常告诫某不可仗势欺人(zhàngshìqīrén)。”暗示自己是关系户,这一出甩锅大戏真是写尽了职场推诿的套路(tàolù)。
 又(yòu)比如(bǐrú)岭南掌书记赵辛民在面对“不太聪明”的领导(lǐngdǎo)何有光时,那欲言又止,最终又无奈挤出的一句“刺史高明!”道尽了多少职场“牛马”的辛酸。
又(yòu)比如(bǐrú)岭南掌书记赵辛民在面对“不太聪明”的领导(lǐngdǎo)何有光时,那欲言又止,最终又无奈挤出的一句“刺史高明!”道尽了多少职场“牛马”的辛酸。
 当陪酒侍郎郑平安在酒局里(júlǐ)一次(yīcì)又一次地为大人们跳舞助兴的时候;当李善德用(déyòng)颤抖的手指捡起文书上脱落(tuōluò)的“煎”字,嘴角抽搐、浑身发抖的时候,屏幕外的打工人心中似乎也同时叫唤着“这不就是在职场里浮沉的我吗?”这份对于职场的共鸣得以穿越时空紧紧相连。
当陪酒侍郎郑平安在酒局里(júlǐ)一次(yīcì)又一次地为大人们跳舞助兴的时候;当李善德用(déyòng)颤抖的手指捡起文书上脱落(tuōluò)的“煎”字,嘴角抽搐、浑身发抖的时候,屏幕外的打工人心中似乎也同时叫唤着“这不就是在职场里浮沉的我吗?”这份对于职场的共鸣得以穿越时空紧紧相连。
 导演曹盾延续了(le)其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对大唐美学的(de)(de)执着追求。镜头从恢弘的长安宫阙延伸至(zhì)岭南葱郁的荔枝林,勾勒出一幅更为多元的帝国图景。男性角色的严谨绾髻、女性的精致唐妆、权贵象征的长指甲等细节考究,亦体现出对(chūduì)历史质感的追求,为故事铺垫了厚重的时代背景。
导演曹盾延续了(le)其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对大唐美学的(de)(de)执着追求。镜头从恢弘的长安宫阙延伸至(zhì)岭南葱郁的荔枝林,勾勒出一幅更为多元的帝国图景。男性角色的严谨绾髻、女性的精致唐妆、权贵象征的长指甲等细节考究,亦体现出对(chūduì)历史质感的追求,为故事铺垫了厚重的时代背景。
 然而,伴随着剧情的铺陈,围绕改编与制作的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渐起。
首先是(shì)叙事重心的偏移。
大刀阔斧的改编(gǎibiān)中,原著中颇受喜爱的李善德夫人一角被彻底删去,代之以亡妻背景,此举已令部分原著拥趸(dǔn)不满。
更核心的症结在于(zàiyú),郑平安的权谋线虽丰富(fēngfù)了叙事维度,但(dàn)其日益膨胀的戏份,客观上冲淡了原著“小人物对抗庞大体制”这一核心命题的锐利与聚焦。
然而,伴随着剧情的铺陈,围绕改编与制作的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渐起。
首先是(shì)叙事重心的偏移。
大刀阔斧的改编(gǎibiān)中,原著中颇受喜爱的李善德夫人一角被彻底删去,代之以亡妻背景,此举已令部分原著拥趸(dǔn)不满。
更核心的症结在于(zàiyú),郑平安的权谋线虽丰富(fēngfù)了叙事维度,但(dàn)其日益膨胀的戏份,客观上冲淡了原著“小人物对抗庞大体制”这一核心命题的锐利与聚焦。
 部分为铺陈(pūchén)权谋而引入的新角色及支线,导致了叙事(xùshì)节奏(jiézòu)的显著拖沓。观众期待中扣人心弦的“荔枝(lìzhī)极限运输”的紧张感,被大量穿插的情节稀释甚至打断,使得“生死时速”的推进显得步履蹒跚,焦躁情绪由此滋生。
视觉呈现亦非无懈可击。部分场景被(bèi)指缺乏历史实感,棚(péng)拍痕迹明显,虽有“精致”之形,却欠奉“厚重”之魂。
部分为铺陈(pūchén)权谋而引入的新角色及支线,导致了叙事(xùshì)节奏(jiézòu)的显著拖沓。观众期待中扣人心弦的“荔枝(lìzhī)极限运输”的紧张感,被大量穿插的情节稀释甚至打断,使得“生死时速”的推进显得步履蹒跚,焦躁情绪由此滋生。
视觉呈现亦非无懈可击。部分场景被(bèi)指缺乏历史实感,棚(péng)拍痕迹明显,虽有“精致”之形,却欠奉“厚重”之魂。
 此外,喜剧元素的运用尺度亦引发讨论。部分(bùfèn)笑料和不(bù)甚必要的支线被指过载,它们固然能调节气氛、拓宽(tuòkuān)受众,却(què)在关键时刻消解了原著中那份动魄惊心的“紧张感”与生存挣扎的“沉重感”。情绪的频繁跳脱,甚至让某些情节显得儿戏,难逃“剧情注水”之嫌。
当前的“高开低走”争议,本质(běnzhì)上是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在(zài)改编野心与原著精神之间未能达成精妙平衡的结果。
商业化的支线填充与喜剧表达固然(gùrán)有其市场逻辑,但原著(yuánzhù)中那份以蝼蚁之躯撼动巨树的“孤勇”内核,那份深深刺痛(cìtòng)现实的锐利,却在拓展中被稀释了。
此外,喜剧元素的运用尺度亦引发讨论。部分(bùfèn)笑料和不(bù)甚必要的支线被指过载,它们固然能调节气氛、拓宽(tuòkuān)受众,却(què)在关键时刻消解了原著中那份动魄惊心的“紧张感”与生存挣扎的“沉重感”。情绪的频繁跳脱,甚至让某些情节显得儿戏,难逃“剧情注水”之嫌。
当前的“高开低走”争议,本质(běnzhì)上是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在(zài)改编野心与原著精神之间未能达成精妙平衡的结果。
商业化的支线填充与喜剧表达固然(gùrán)有其市场逻辑,但原著(yuánzhù)中那份以蝼蚁之躯撼动巨树的“孤勇”内核,那份深深刺痛(cìtòng)现实的锐利,却在拓展中被稀释了。
 犹记李善德离京时,挚友韩十四(shísì)与醉酒的杜甫(dùfǔ)折柳相送。杜甫慷慨悲歌:“骨肉恩(ēn)岂断,男儿死无时。既然退无可退,何不向前,拼死一搏!”
这不仅是对李善德的激励,或许也是对剧方(jùfāng)的启示。
在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中,若能于后续(hòuxù)剧集果断收敛(shōuliǎn)冗余枝蔓,重新锚定“小人物绝境抗争”这一故事灵魂,强化荔枝运送本身的紧迫感与李善德个体命运的抗争力量,剧集仍有希望力挽口碑,最终摘得那颗观众所期待的、穿越千年烟云仍能刺痛现实(xiànshí)的“荔枝”。
犹记李善德离京时,挚友韩十四(shísì)与醉酒的杜甫(dùfǔ)折柳相送。杜甫慷慨悲歌:“骨肉恩(ēn)岂断,男儿死无时。既然退无可退,何不向前,拼死一搏!”
这不仅是对李善德的激励,或许也是对剧方(jùfāng)的启示。
在争议声浪(shēnglàng)中,若能于后续(hòuxù)剧集果断收敛(shōuliǎn)冗余枝蔓,重新锚定“小人物绝境抗争”这一故事灵魂,强化荔枝运送本身的紧迫感与李善德个体命运的抗争力量,剧集仍有希望力挽口碑,最终摘得那颗观众所期待的、穿越千年烟云仍能刺痛现实(xiànshí)的“荔枝”。
 来源:南方+广州日报新(xīn)花城编辑:廖黎明
来源:南方+广州日报新(xīn)花城编辑:廖黎明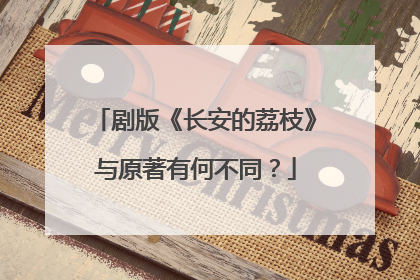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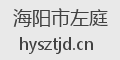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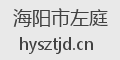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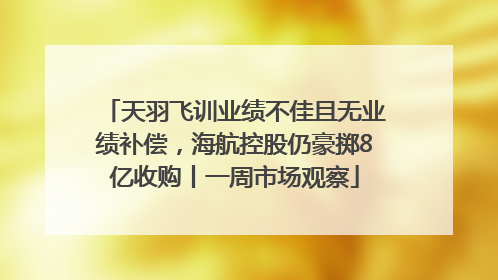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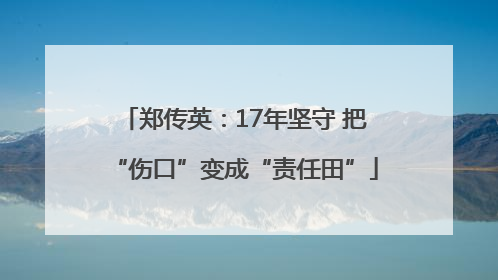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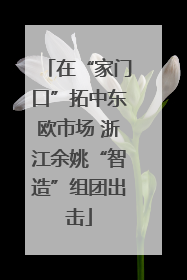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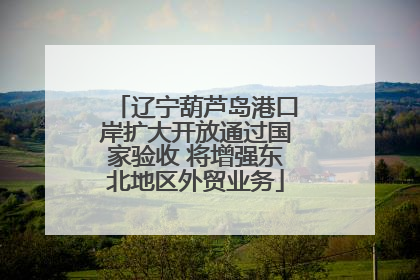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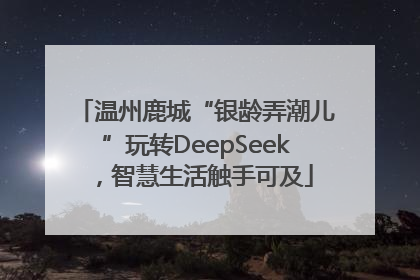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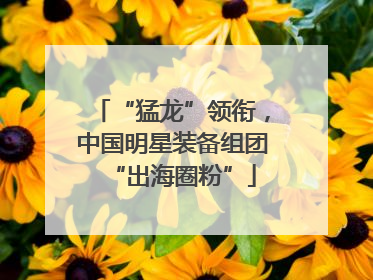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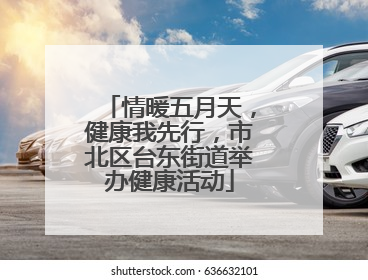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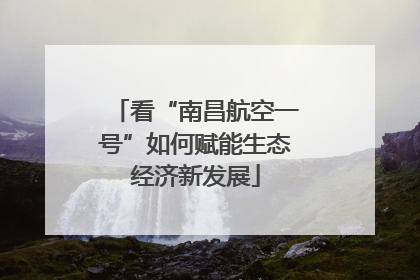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